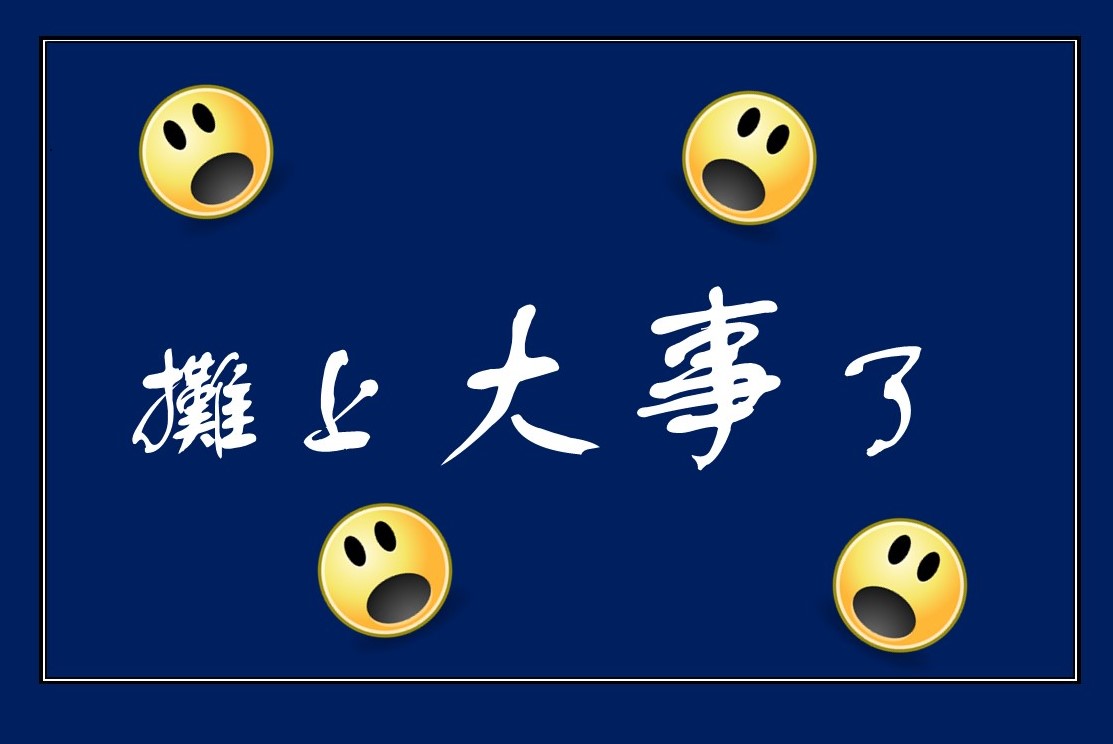鄙人習慣書寫天主教事務,但這次卻想從佛教説起。
1月20日,新聞報道了四川佛教協會副會長釋照杰因偷情女主播的醜聞,被撒銷四川省政協委員資格。該宗醜聞是去年初女主播丈夫再次威脅釋照杰索要巨額金錢,換取不曝光其與女主播被偷拍不正常關係的視頻,才導致釋照杰報警抓了女主播夫婦。案件於去年11月開審而為外界所知,並因此惹來對佛門清修之地出現此等桃色醜聞的關注。
奇怪的是,去年秋季天主教也有一位大佬出了事,且聽聞同樣是極其嚴重、鐵板釘釘的大事,可至今快半年卻一直沒見曝光,時至今年初才有更多教友從教會新聞中開始發現不對勁。
這位教會大佬是誰,咱就不開名了,繼續看下去定能猜到,因為大佬近年的際遇,已被外界形容為「棄子」。當年甘願成為非法主教,命中注定只能淪為別人的棋子、政治籌碼,可用也可棄。當被發現政治不忠,做不到政治上的明白人,自然就不用給「棄子」留任何情面了。
首先讓我們回到2018年,教會大佬在西南某省的主教座堂被指違章建築,比規定範圍多出五成。當時有報道說,當局邀請他回省商議,大佬卻避而不去,結果眼巴巴被拆。據聞,當時大佬在京城不同部門做遊說功夫,但為他撐腰者卻力不從心。說到此事,教會信徒即使不相信因果,但華人還是會講善惡有報。這座主教座堂2008年批准重建,教會大佬於2010年成為一會一團的高層,主教座堂的建造亦水漲船高,便參與當地的「地鐵101項目」,與合作商開設「天主教自養管理中心」來銷售店舖。怎料,在竣工前夕,教區刊登聲明指與自養中心無關,業主和自養中心簽訂的合約均屬無效,從而鬧出欺詐風波,涉及近二百名苦主、上億元人民幣。據說部分受害者是用畢生積蓄去投資,結果血本無歸。大佬當時的事業在上升軌道,想不到後來地方保護傘倒台,投資者於2017年抗議行騙,告上法院,連累教會形象;2018年更出現了違章的指控。主教座堂是標誌一個教區的主教坐鎮的聖堂,這樣說拆就拆,還不是打臉?
可能教會大佬還未意識到自己烏雲蓋頂,倒霉的日子早已臨頭。2022年召開的第十次全國天主教代表會議,一會一團兩位最高級領導人同時退下,擔任榮譽主席。在近十年間的新政風氣之下,退休官員基本上已沒有影響力。然而,這位退下來的大佬卻退而不休,仍高調摻和一會一團的事務,給人仍有影響力的印象,為的是不容易被人看出棄子的命運。可是棄子越是要遮掩,越是捉襟見肘。2023年初,第十四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換屆,在十一名天主教代表中,身為一會一團兩名榮譽主席之一的教會大佬連政協委員都不是,而另一位榮譽主席卻當上政協常委,對比之大,明眼人一看便知,這應該是有意要讓外界知道他已走進末路。
可惜教會大佬的政治智慧不足,繼續製造新聞和事端。2023年4月,全世界都知道沈斌當上了上海教區主教的職位。然而,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即使在就職禮的前夕,有關教區得到的消息竟是由該名教會大佬空降掌管。大佬的這個多年心願是眾人皆知,但如何能把有關教區矇騙至最後一刻,倒也煞費苦心。可能寶座落空,感到非常失落的大佬,尋求慰藉而終於發生了去年秋季的大事。
說到這裡,大家可能已猜到教會大佬的身份。事實上,去年12月在上海舉行的一會一團會議,本來愛摻和的大佬不尋常的缺席已引起教會內私下的議論與猜測。緊接著今年1月底,該大佬所在的省天主教會舉行為期三天的第五次代表會議,從照片上,大佬雖然列席會議,但卻沒有在新一屆兩會的領導班子中有任何頭銜,連監事會也沒份做。一般來說,即使在一會一團退任,在地方兩會多維持領導職務。這是不是考慮到大佬之事不能一直掩著摀著,先讓他退出江湖,作為事件一旦公開的舖墊?
教會大佬的一再失落,照理一般人不會害怕議論,如今攤上大事半年時間都仍能秘而不宣,讓人更生好奇。這是對個別宗教特別優待而網開一面?還是不忍傷害與教廷近年所建立的「密切關係」的「大好勢頭」?問題是教會內從來都知道教廷對教會大佬並無真正的好感,他的失落是否對教廷有所「傷害」卻又從可談起?不過話說回來,前兩星期看到一篇外語的教會評論,作者指出,普世教會往往對發生醜聞的主教,都是讓他們稱病退位。教會大佬的主教職務,會否因其發生的鐵板釘釘大事而受影響?是否稱病退隱,我們就拭目以待吧!